1.何為代參
“代參”何意,“代”即代表代理,“參”即參加參觀,因而“代參”即作為代表去參加活動。而為什么要代為參加呢,因為有人有事去不了,或正趕上農忙季節抽不開身,可是泡溫泉又不是非固定于某個時間上的事,即便現在有事,等沒事時再去也無妨,因而“有事說”又說不過去。也可能是節事的原因吧,節日是一定要在固定的日子里舉行的,那么若是在節日里去不了,那就需要被“代參”了。
即不管怎樣,“代為表達”或“代為購買”等在過去是很常見的事情,出現“代參”乃情理之中。就像在“文革”期間有人去上海出差,鄰居們就都托其代買這個買那個,因為那時物質不豐富,有些東西只有在大城市可以買到,上海的東西質量好也時尚,進城辦事的人也往往代村民買東西。
2.真實的原因:不富裕
“代參”真正的原因是錢的問題,因為過去都不富裕,而前往參拜是需要花路費的,需要住宿和盤纏,因而工作忙沒時間僅僅是一個方面的原因。但那時的人們還是有參拜的欲望,他們希望去泡溫泉治病,過去的人積勞成疾也是常見的事,因而形成了派代表去參拜的習慣,那時的人們也是很相信“神”的。
如何平衡想去參拜而又沒錢的關系,如此就發明了“代參”形式以解決矛盾。比如今年你去,明年他去,后年我去,大家輪換著來,如此就都能去上,但錢是大家一起齊上來的。即大家每年都要交錢,但自己幾年才能去一次,自己去不了的那年,要由去的人代為自己參拜,當然回來時可能還會帶回禮物來。

故除溫泉地居民外,歷史中的日本百姓往往是通過巡游、巡禮與參拜等形式把溫泉地與朝圣的宗教活動串聯性地結合起來的,那情景很有點想英國的“大旅游”,人們先去泡溫泉接受治療或沐浴——到箱根湯本溫泉宿一晚,之后再“順道”或“繞道”去參拜一些著名的寺院或神社如伊勢神宮,在回程時再游覽京都,后去善光寺參拜,然后到伊香保溫泉等。那時的參拜是以農民團體形式進行的,這也解釋了“參”這個字的語義——加入其中,當時即出現了“代參”的文化現象。
4.“過去的百姓被管得很嚴”
即便是在日本,過去的日本百姓也是被當局管理得非常嚴格的,平時是不允許隨便外出的,百姓需要持有批準文書才能外出,這讓筆者想到了曾經年代的“介紹信”與“糧票”——上世紀70年代。人若是流動了,雖然這讓社會有了“活力”,但因此也具有了“江湖性”,那就不好管了,因為路人彼此間是不認識的,行為或因此“失范”,所以怕出事的第一反應都是限制百姓外出。
但有一種情況例外,那就是外出參拜神社或去湯治,在這種情況下,日本百姓們通過申請是可以得到批準的。故為了敬神與為了治病,日本早年的統治者允許百姓外出,哪能治病還不讓出行呢,哪能敬神還不讓外出呢,日本社會自古以來就認為人是需要敬神的,也是要敬畏于泡溫泉治病的,那就是在敬畏生命。

“參”即“參加”,似乎沒啥可解釋的,即加入其中。但我們習慣于說“參加”,不愿意說“加參”,即我們很喜歡強調自我,而不愿意強調自己是其中之一,也即我們的自我意識很強。所以“參加”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常用詞匯,而“代參”往往不是我們的詞匯。即雖然我們可以理解“代參”的意思,但我們自己一般不說“代參”。
即我們確實參加了,但誰會強調其他人了?誰會強調與他人的關系而弱化自己?我們以“更大的比例”關心于我們自己,所以除了“參加”,也可以說“參拜”、“參觀”, 但不說將“參”做后綴的詞——除了“人參”,當然“人參”的“參”字發音變了。
我們確實有“高參”之說,但這樣的詞太少了,還加了一個褒義字“高”,或可以認為自己的“參”還是很偉大的。即雖然在很多情況下自己是其中之一,但卻不愿意承認那個“之一性”,想強調接下來是自己獨立發揮作用的,是自己的眼睛在“觀”——“參觀”等,那是“在參觀之中而自己獨立思考”的與他人無關。
6.“可參性”
假如能弱化一下語言上的自己的作用與地位,別把自己看得那么高,而是關注自己與其他的關系,那么就可以發現很多新詞,其實就是調換一下原有的詞的詞序。如“參觀”變“觀參”,就提示著有些事是可以大家一起看的,比如劇場就具有觀參性。筆者有時也喜歡去超市或農貿市場轉轉,那也是在利用那種“可參性”——并無具體交流對象的散散心。依照這樣的思路,可有“加參”其中說法,還可以說“天參”——都市里又多了一座摩天建筑。在戲詞中就有“參了一狀”、“參你”等說法,顯然那還不同于“告狀”,那是不是指也跟著他人告了其一狀的意思呢——即告狀的不止我一個。

都知道“參”的讀音,而為什么發那個音呢,即其與“餐”同音。在家里面吃飯時,大家都圍成一桌,還真是“參”的情景,大家一塊吃一塊怎樣那就是“參”——在其中。因而“參”是大家一起的,自己匯入其中的,而且那一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,重要得如同吃飯一樣。而向我們散步時走到了街上,與街人走到一起了,匯成了“人的流動”,那就不能說“參”了,因為“散步”不是什么大事,但參加游行那就是“參”。
當“參”是動詞時念“餐”,而若是名詞的話,那就念“身”,即地里雖然種了很多的人參,一個個在地下“插”著,可以想象那個地下情景,那就是一種“參”,每一個“胡蘿卜”在地下都“參”著,都是加入其中而成為其中之一,但就一個而言,那就是果實的“身”——就像我們身體,所以“人參”、“黨參”的“參”都念“身”。就像我們體“參”( cān)于社會,但我們的身體卻是體參(shēn,身)。
8.“參性”與地域環境
任何民族應該都意識到這個“參性”,至少是漢文化的造字者意識到了,但是不是這個社會對此有明確的認識,那可就不一定了。有的民族這方面意識強,較為全面地懂得“參”的意思,也能通過“參什么”與“什么參”平衡地造詞與用詞,強調我在其中,因而會經常說“代參”,而有的民族會說“參加”,將“參”作為修飾,而強調“plus me”的“加性”——強調我的“核心作用”。
換言之假如是“島國”,“島國人”是不是很虔誠,是不是很重視“參”,因為島國太小了。而若是人口數量規模大,人口高密度,那就會更關心“人間性”的什么,即若是不強調自己,個人的權利是不是很可能就會埋沒了,因而此時會不會就不太強調“代參”,而是強調“參加”。
再有當國土遼闊而走不到邊,我們可以就地怎樣,但也可以通過遷徙而換個地方,那么就可“參”也可“不參”。而島國的人是沒地方走的,因而島國居民只能“參”入其中,因而他們很注重禮節,就怕被踢出“群”,所以會注重產品質量,也會注重人之間的約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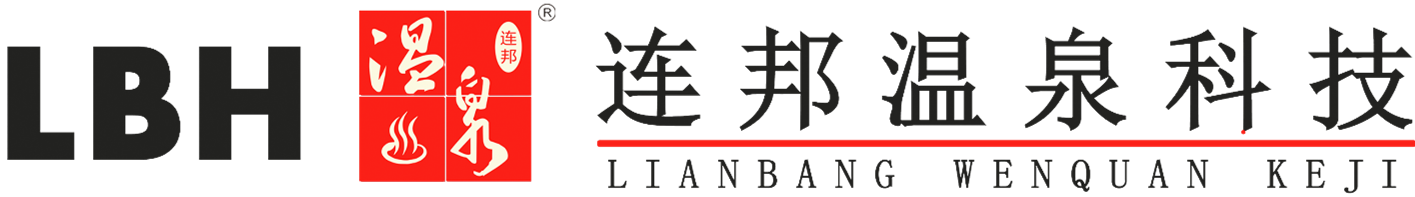
 當前位置:
當前位置:





